第三十四章 虽然无所长 名可由行立(2/4)
“有。”
张 伏拜说道“便服临军,显明公之从容;折氾太守,显明公之正;端坐晏然,足可见明公的雅量;送刀不悔,是明公守信;拒婢不取,明公之诚是不夺
伏拜说道“便服临军,显明公之从容;折氾太守,显明公之正;端坐晏然,足可见明公的雅量;送刀不悔,是明公守信;拒婢不取,明公之诚是不夺
 。明公又有救
。明公又有救 之义举。明公的声名早就应该响彻国中了,之所以至今无闻者,是因为明公谦厚,未尝炫耀2。”
之义举。明公的声名早就应该响彻国中了,之所以至今无闻者,是因为明公谦厚,未尝炫耀2。”
从张 问第一件事起,莘迩就心存疑惑了,这些事
问第一件事起,莘迩就心存疑惑了,这些事 大多发生在郡府或者外郡,张
大多发生在郡府或者外郡,张 怎么得知的?听他说到“未尝炫耀”,便打断问道“我这几件事,你怎么知道的?”
怎么得知的?听他说到“未尝炫耀”,便打断问道“我这几件事,你怎么知道的?”
张 答道“
答道“ 听张道将和郡吏说的。”
听张道将和郡吏说的。”
莘迩恍然,点了点 ,说道“你继续说。”
,说道“你继续说。”
“ 闻明公与傅公
闻明公与傅公 好。可是么?”
好。可是么?”
“不错,我俩患难之 。”
。”
“傅公 得本郡士
得本郡士 的尊敬,
的尊敬, 常与郡县名士宴会,如果能够使傅公为明公扬名於上流,
常与郡县名士宴会,如果能够使傅公为明公扬名於上流, 敢请为明公张誉於民间,年月之中,明公之名,定然举国皆知。此为上策,弊在较缓。”
敢请为明公张誉於民间,年月之中,明公之名,定然举国皆知。此为上策,弊在较缓。”
莘迩心道“原来他的上策是找公关,给我包装。这个办法虽说是见效慢了点,但光明正大,是长远之计,比那急功近利的行贿之法要强得多。
“……,只是,会水县那事儿是我特意为之的,给我扬扬此名倒是甚好,取信於胡,出自黄荣的建议,我自觉亦是不错,也可传扬;老氾、张道将、老傅那事儿,却也值得鼓吹么?”
他觉得这三件事都是小事,甚至张道将那事儿还让他挺没面子的,并不足以当做吹嘘的资本,但细细品味张 的话,这三件事到了他的嘴里,还真是不太一样了,听起来挺不错的。
的话,这三件事到了他的嘴里,还真是不太一样了,听起来挺不错的。
莘迩不禁又心道“话凭一张嘴。被张 这么一说,我似乎、也许、好像,嘿嘿,还真是金光闪闪,满身优点了啊。”
这么一说,我似乎、也许、好像,嘿嘿,还真是金光闪闪,满身优点了啊。”
张 在张家多年,张金是个邀名养望的高手,张家平时来往的又多是所谓的名士,因此,对於名流士
在张家多年,张金是个邀名养望的高手,张家平时来往的又多是所谓的名士,因此,对於名流士 们的名声都是怎么来的,张
们的名声都是怎么来的,张 再清楚不过了。
再清楚不过了。
士 们每天的生活都很清闲的,哪儿来那么多的雅事传出?除了少数外,大多都是互相吹捧出来的。哪怕芝麻烂谷子的
们每天的生活都很清闲的,哪儿来那么多的雅事传出?除了少数外,大多都是互相吹捧出来的。哪怕芝麻烂谷子的 事,只要包装得好,只要有
事,只要包装得好,只要有 宣扬,那传出去就是雅事一件。
宣扬,那传出去就是雅事一件。
如那张金,
 在家,起居饮食罢了,何来那般大的名声?便是由此得来。
在家,起居饮食罢了,何来那般大的名声?便是由此得来。
寻常名士们的获名之道大凡这般。不过,此道说来简单,做起来却难。难在何处?难就难在“圈子”二字上。一流的士族自成一圈,二流、三流的想挤进去,挤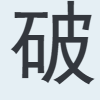
 也难。
也难。
莘迩目前所缺的,就是圈子。
他不在名士们的那个圈子中,名士们 嘛要理会他?
嘛要理会他?
但有了傅乔就不同了。
傅乔乃定西国的清谈 将,不仅在这个圈子里,且是这个圈子中最为瞩目的之一,只要有他帮莘迩宣扬,假以时
将,不仅在这个圈子里,且是这个圈子中最为瞩目的之一,只要有他帮莘迩宣扬,假以时 ,莘迩的名声必然远播。
,莘迩的名声必然远播。
莘迩定住心神,笑道“君之上策,胜於下策。”
张 给张家的出谋划策,上策罕见得用,通常只行下策,改换门庭之后,这是
给张家的出谋划策,上策罕见得用,通常只行下策,改换门庭之后,这是 次给莘迩进策,忽然闻他要选上策,张
次给莘迩进策,忽然闻他要选上策,张 只疑听错,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,说道“明公如取上策,
只疑听错,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,说道“明公如取上策, 以为,可先择傅公、氾太守两事向外传播。”
以为,可先择傅公、氾太守两事向外传播。”
莘迩“哦”了一声,心道“先择傅、氾两事?”旋即领会了张 的意思。
的意思。
五件事如果一起推出,繁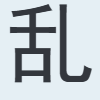 是一,且会显得刻意,所以不如慢慢地拿出来。
是一,且会显得刻意,所以不如慢慢地拿出来。
而先取傅、氾二事,则是因为此两 名气大。
名气大。
既然博名,当然是事件中涉及的对方越出名越好。攀龙附凤,即此意也。
听完了张 的上策,莘迩踌躇心道“我是个忠厚
的上策,莘迩踌躇心道“我是个忠厚 ,搞这等自吹自擂的事
,搞这等自吹自擂的事 ,实在羞惭。……要紧的是,我如何开
,实在羞惭。……要紧的是,我如何开 对老傅说呢?”
对老傅说呢?”
担心傅乔会笑话他,脸面上挂不住。
张 见他沉吟,大概猜出了他的犯难,说道“傅公、氾太守两事中,傅公之事,其实对他也有益处。赠婢於友,风雅事也。
见他沉吟,大概猜出了他的犯难,说道“傅公、氾太守两事中,傅公之事,其实对他也有益处。赠婢於友,风雅事也。 以贱躯,冒昧敢请明公介荐,为公拜访傅公,述说此意。”
以贱躯,冒昧敢请明公介荐,为公拜访傅公,述说此意。”
莘迩大喜,痛快地应道“好!”
时下阀族当政,士 间的结
间的结 礼仪比前代更严,不仅只是需要有
礼仪比前代更严,不仅只是需要有 介绍,并且地位不等的,即使有
介绍,并且地位不等的,即使有 介绍,往往其中一方也不会与之结
介绍,往往其中一方也不会与之结 ,话都不会接一句3。
,话都不会接一句3。
张 与傅乔不认识,因此,他要去拜见傅乔的话,就需要有个同时认识他俩的
与傅乔不认识,因此,他要去拜见傅乔的话,就需要有个同时认识他俩的 作个中间的介绍
作个中间的介绍 ;而又因他知道自己比傅乔的名声、地位远低,故此有“贱躯”、“冒昧”之语。
;而又因他知道自己比傅乔的名声、地位远低,故此有“贱躯”、“冒昧”之语。
莘迩当即写书一封,给予张 。
。
张 接住收好。
接住收好。
莘迩请他 榻,重拾话
榻,重拾话 ,又问起了最关心的问题“君现在可以说为‘与不为之’道了吧?”
,又问起了最关心的问题“君现在可以说为‘与不为之’道了吧?”
——
1,博闻强记因为这个是当下士 与前代大不相同的风尚,与时代之文化背景密切相关,而如写
与前代大不相同的风尚,与时代之文化背景密切相关,而如写 书中,未免影响阅读的流畅,所以在此章末作个小注。
书中,未免影响阅读的流畅,所以在此章末作个小注。
本章未完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